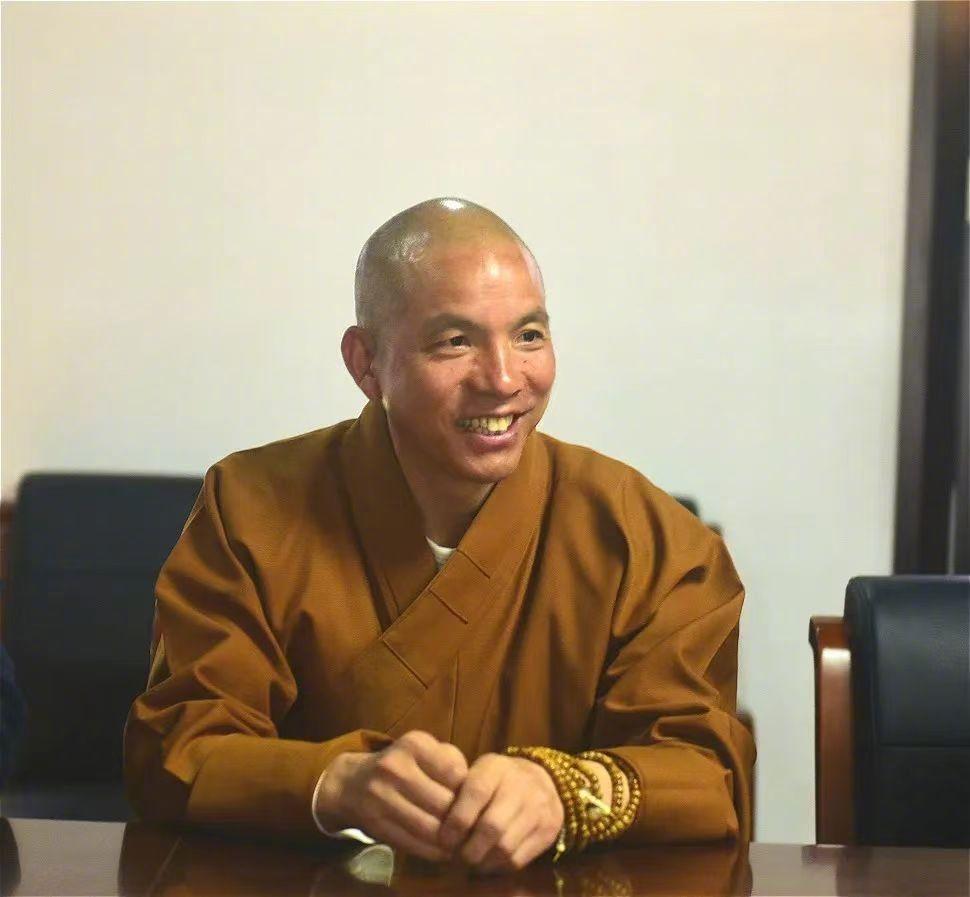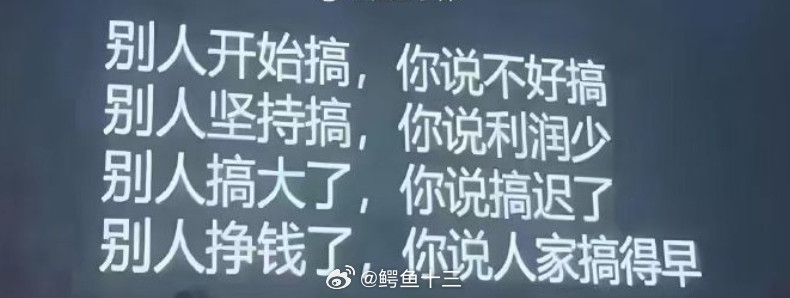汉景帝废了太子刘荣,然后问刘彻:你想当天子吗?景帝本以为小刘彻会说想,谁知道,刘彻稚声稚气冒出一句:这事由天不由我,儿只想天天待在宫里,陪着陛下,不敢偷懒,忘了做儿子的本分。这话说得,景帝直接愣在当场,像是被雷劈了似的。才几岁的小孩儿,咋就这么会说话?
长安城,未央宫里的气氛比寒风还冷。太子刘荣被废黜,贬为临江王。消息传开,朝野震动。宫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,生怕弄出一点声响。废太子的生母栗姬,被幽禁在冷宫深处,日夜啼哭。偌大的宫殿,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。
景帝刘启独自坐在宣室殿里,面前的奏章堆得老高,他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废黜长子,他心里并不好受。刘荣是懦弱了些,可终究是他看着长大的儿子。但为了大汉江山,为了身后安稳,他不得不狠下心肠。
储位空悬,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,让他寝食难安。几个儿子各有心思,背后牵扯着不同的外戚势力,怎么选?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
殿门轻轻推开,一个矮小身影走了进来:“儿臣刘彻,拜见父皇。”景帝抬眼望去,是他第七子刘彘(后改名刘彻),才七岁多点,小脸圆润,眼睛又黑又亮。
这孩子是王美人所生,景帝平日里也颇为喜爱,但从未想过他会与储位有什么关联。今日心烦意乱,便想看看这个最小的儿子,图个清净。
“彘儿,过来。”景帝招招手,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疲惫的温和。刘彻迈着小步走近,在父亲面前站定,仰着小脸,眼神清澈,不躲不闪。
景帝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脸庞,心里那根紧绷的弦似乎松了一点点。他忽然起了个念头,一个带着试探,也带着几分自嘲的念头。他微微俯身,看着刘彻的眼睛,用一种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口吻问道:“彘儿啊,告诉父皇,你想不想…将来也坐在这龙椅上,当天子啊?”
这话问得轻飘飘,落在空旷的大殿里,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深潭!侍立在旁的几个老太监,头垂得更低了,恨不得把耳朵也塞起来。天子之位,岂是能随口问的?尤其在这储位悬空的时刻!
景帝问完,自己心里也微微一紧。他预想了几种回答:孩子或许会懵懂地点头说“想”,那便一笑置之;或许会害怕地摇头说“不敢”,那也是常情。他等着看这小儿如何应对。
刘彻脸上没有一丝惊慌,也没有半分迟疑。他挺了挺小胸脯,用那清脆得如同玉磬敲击般的童音,一字一句,清清楚楚地说道:“父皇,当不当天子,那是老天定的,儿臣说了不算呀!儿臣只想天天在宫里,陪着父皇,好好读书,好好听父皇的话,不敢偷懒,更不敢忘了做儿子的本分!”
话音落下,整个宣室殿静得可怕!连殿外呼啸的风声似乎都停了。
景帝脸上的那点温和笑意瞬间僵住!他像是被一道无声的惊雷劈中,整个人定在了那里!眼睛瞪得溜圆,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还不到他胸口高的儿子,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,夹杂着巨大的惊愕和难以置信,从脚底板直冲头顶!
这孩子才多大?七岁!寻常人家的孩子,七岁还在玩泥巴、追鸡撵狗!可他说出的话…“由天不由我”——轻飘飘一句,就把那烫手的皇位推给了天命,撇清了自己所有可能的野心!这滴水不漏的回答,这深谙分寸的智慧,简直像个在朝堂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狐狸!
景帝只觉得一股寒气顺着脊椎骨往上爬。他下意识地攥紧了龙椅的扶手,指节捏得发白。这孩子…这孩子背后是谁在教?是那个温婉娴静、从不争宠的王美人?还是…他背后那些看似低调的王家外戚?
一个七岁的孩子,心思竟能如此深沉?景帝越想越心惊,后背竟隐隐渗出一层冷汗。他看着刘彻那双依旧清澈、似乎毫无杂质的眼睛,第一次感到了深不可测的寒意。这孩子,是璞玉?还是…妖孽?
刘彻说完,依旧规规矩矩地站着。景帝喉头滚动了一下,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,干涩地挤出一句:“好…好孩子…说得很好。”他挥了挥手,声音有些发飘,“下去吧…好好读书。”
“儿臣告退。”刘彻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,转身迈着小步,不疾不徐地走出了大殿。
景帝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里,久久没有动弹。废黜刘荣带来的沉重,被方才那番对话搅得更加纷乱。他反复咀嚼着刘彻那几句话,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。
这孩子,要么是天赋异禀,聪慧得可怕;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,心思深沉得令人胆寒。无论哪一种,都让他这个做父亲的,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和一丝莫名的…忌惮。
殿外的日影一点点西斜,将景帝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疲惫地闭上眼,靠在龙椅上。立储之事,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这个七岁的幼子,如同一颗突然闯入棋局的、让人看不清分量的棋子,让这位掌控天下的帝王,第一次在深宫之中,感到了天威难测之外的另一种寒意——来自血脉深处,却又难以捉摸的寒意。
几年后,当景帝最终下诏,立七岁的刘彘为太子,并为其改名“彻”时,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宣室殿里那个冬日午后,那个稚子口中吐出的、如同惊雷般的话语。帝王之路,从来布满荆棘,而那个七岁孩童清澈眼眸下隐藏的究竟是赤子之心,还是早已洞悉了权力游戏的早慧,或许只有深宫高墙内流转的岁月,才能给出答案。